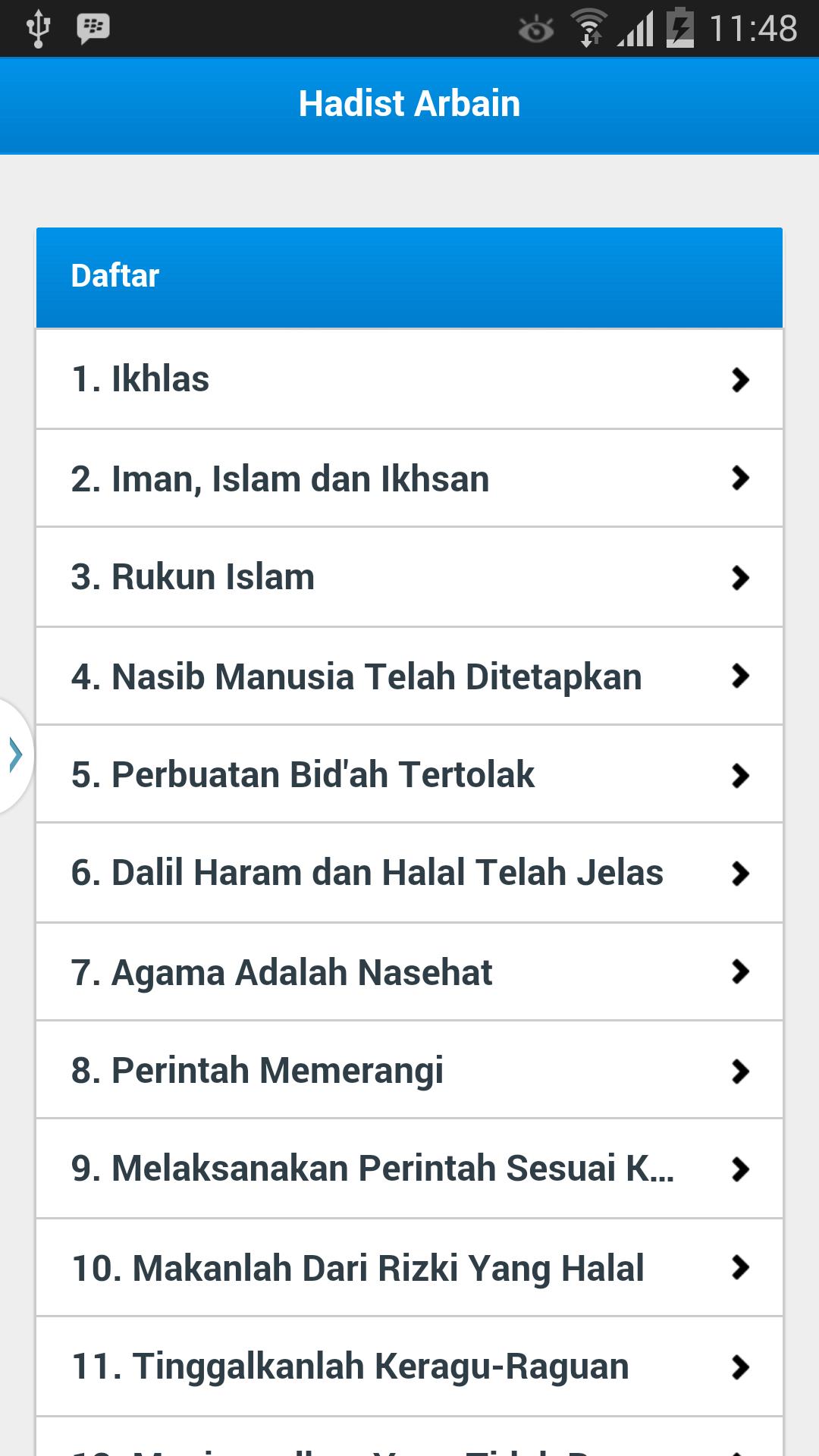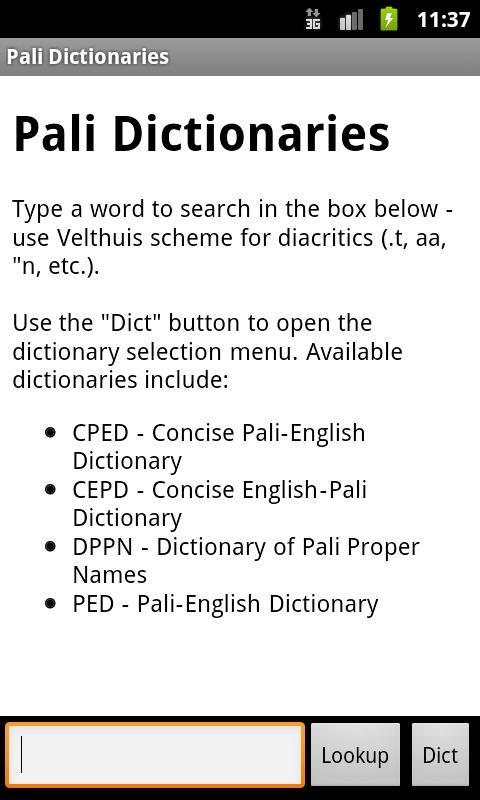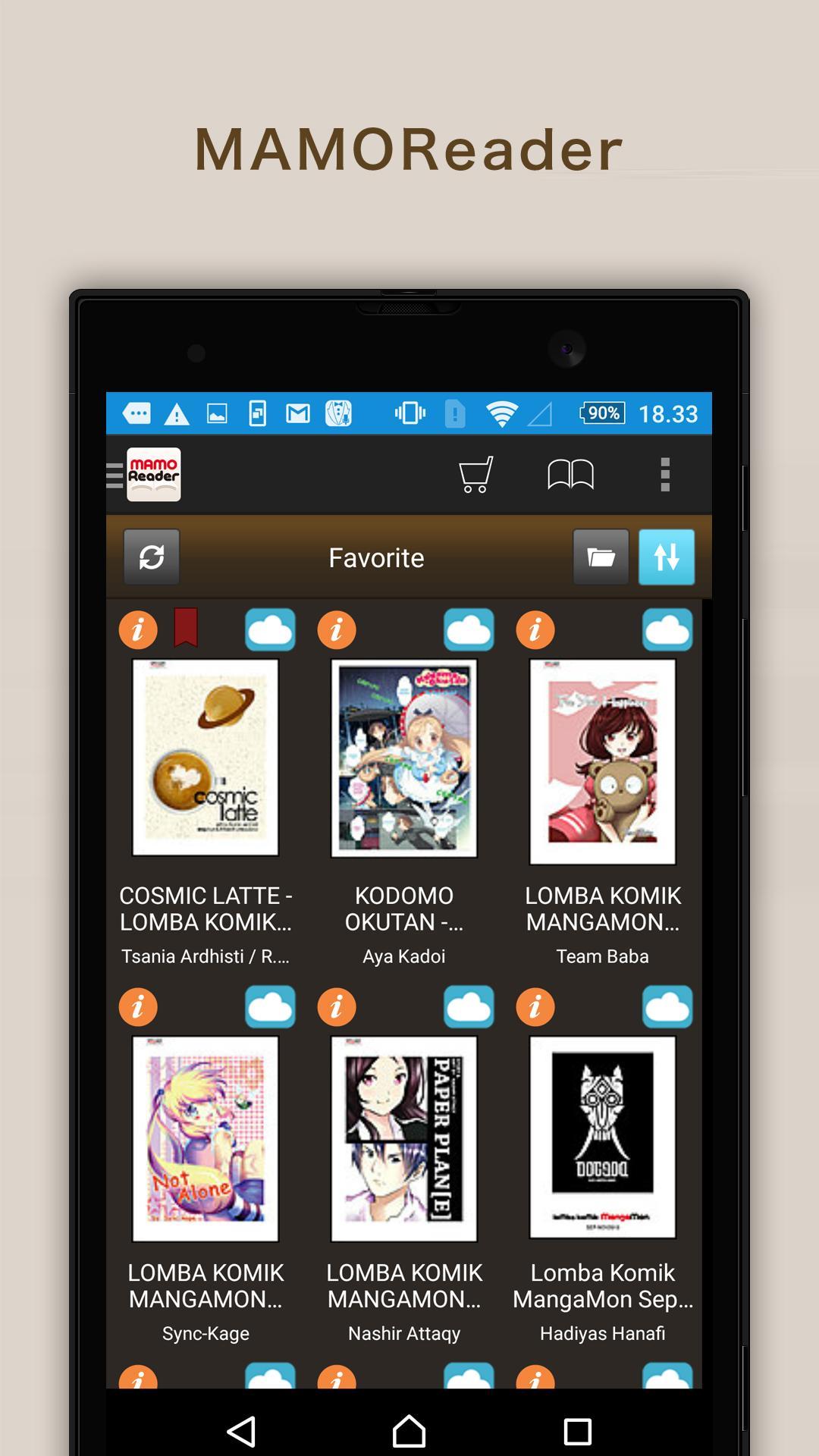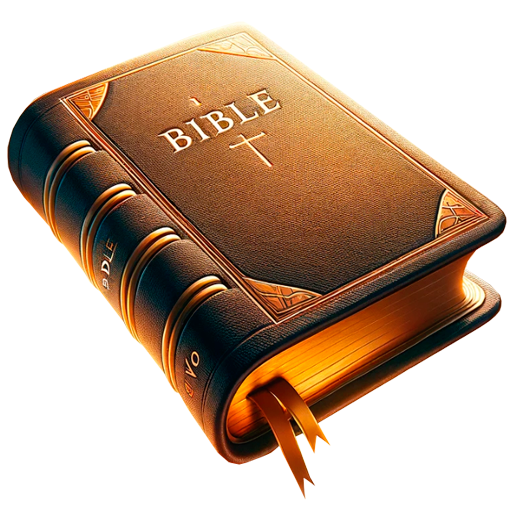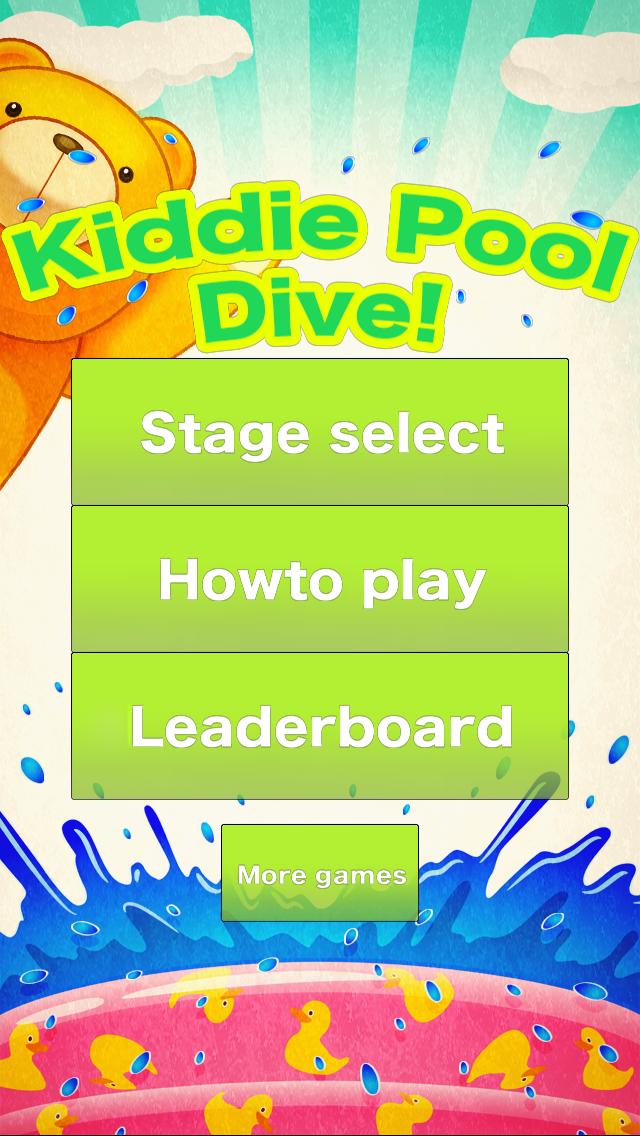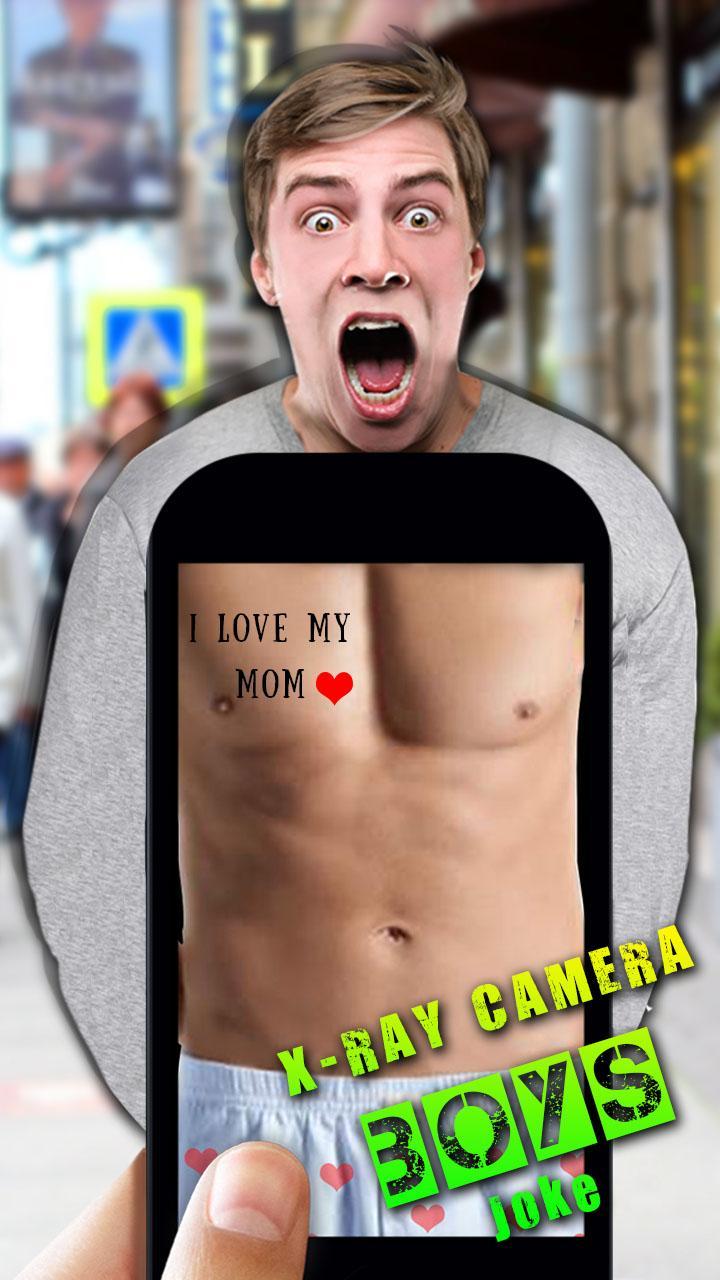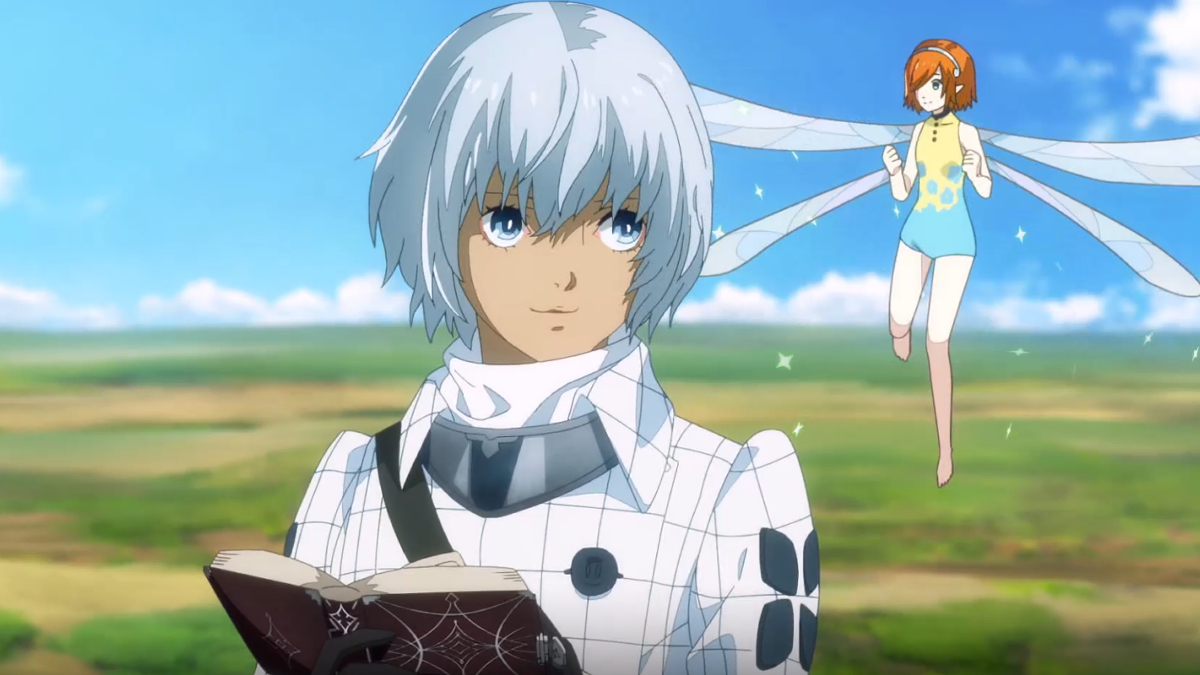一个人应该只在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方说话,只谈论一个人被征服的东西 - 其余的都是chat不休,“文学”,不良的繁殖。我的著作只谈到了我的征服:“我”在其中,对我的一切敌意,自我ipsissimus,或者,如果允许更傲慢的表达方式,则自我ipsissime。可能猜测我下面有很多。但是,首先,我总是需要时间,康复,距离,分离,然后才感到渴望扑倒,破坏,裸露,代表“代表”(或任何一个喜欢称呼它的人)的渴望,以获得世界的其他知识,这是我所生活和超越或忍受的,做事或遭受了某些事情。因此,我所有的著作,一个例外,重要的是,这是事实, - 必须过时 - 他们总是讲述“我的落后者”。有些甚至像季节后的前三个想法一样,必须在创作和经验的经验之前(被引用的案件中的悲剧诞生,因为任何具有微妙的观察和比较能力的人都无法理解)。反对老式戴维·斯特劳斯(David Strauss)的德国主义,自鸣得意和演讲的破烂,这是第一个经过季节后的第一个经历的内容的爆发,这给我引发了一种感受,在德国文化和文化的非凡主义者中很久以前就激发了我的感觉(我声称了现在使用过的菲尔斯的养老药,``我宣称过多地使用过的菲尔态''我对“历史疾病”的说法是,我说的是一个慢慢而费力地从这种疾病中康复的人,并且根本没有在将来放弃“历史”,因为他过去曾遭受过她的苦难。当我在第三个季节中思考时,我表达了我对第一位和唯一的老师的敬意,那是我的亚瑟·舒佩纳豪(Arthur Schopenhauer) - 我现在应该给它一个更加个人化和强调的声音 - 我已经在我的角色中陷入了道德上的怀疑主义和散布的痛苦,这也是如此,这与当今的批评一样,与当今的批评相同。正如人们所说的,我已经不相信“有福的事情”,甚至在Schopenhauer中也不相信。正是在这个时期,我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“从道上的意义上讲真相和虚假”就开始了。即使是我为纪念理查德·瓦格纳(Richard Wagner)纪念理查德·瓦格纳(Richard Wagner)的礼仪演说,在1876年在拜罗斯(Bayreuth)在拜罗斯(Bayreuth)举行的胜利庆祝活动之际 - 贝拉瑞特(Bayreuth)表示,艺术家赢得了最大的胜利,这是一部最有力的“个性”邮票,在我的事实上,这是一个最平静的事实,但它是一个平静的事实,这是一点点的态度,而这是一点点的态度,而这是一点点的事实,而这是一点点的态度,而这是一定的事实。遣散和告别。 (理查德·瓦格纳(Richard Wagner)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吗?我不这么认为。只要我们仍然爱,我们不画这样的图片,[pg 003]我们还没有“检查”,我们不会将自己放置在这么远的地方,因为对一个人来说,对一个人进行“检查”。几乎没有理解。)镇定使我有能力在经过多年的孤独和戒酒之后发言,首先是书《人类》,《太多人》,第二个序言和道歉是专门的。作为“自由精神”的书,它显示了心理学家几乎开朗和好奇的寒冷的一些痕迹,他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痛苦的事物,并为自己建立了自己的痛苦,并为自己确定了它们,并像针头一样牢固地修复了它们。是否会不时地奇怪,这是一种又一遍地的滴答作用,那就是心理学家的手指上,不仅在手指上都有血吗?